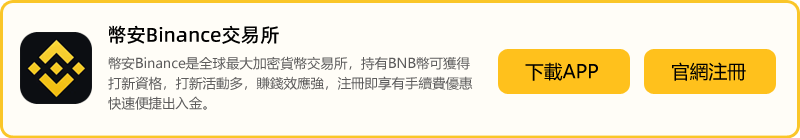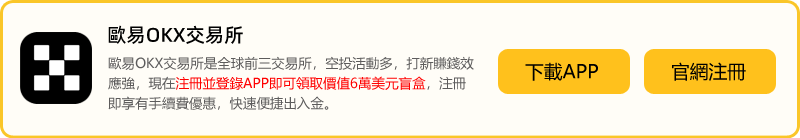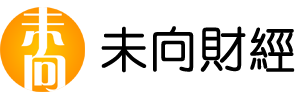《人民法院報》重磅刊文:虛擬貨幣不是法外之地,三種情形構成犯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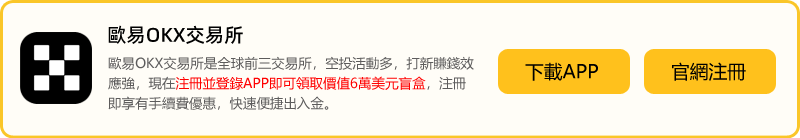
文中指出,虛擬貨幣結算支付型幫助行為是運用虛擬貨幣為他人實施電信詐騙提供財物轉移幫助的行為。
本文首刊於《人民法院報》
作者:石經海蘇青西南政法大學
10月26日,人民法院報刊文《虛擬貨幣結算支付型幫助行為的犯罪認定》。文中指出,虛擬貨幣結算支付型幫助行為是運用虛擬貨幣為他人實施電信詐騙提供財物轉移幫助的行為。在虛擬貨幣結算支付行為的犯罪認定中,應掌握犯罪所得的特徵,上遊電信詐騙與後續掩飾、隱瞞犯罪所得及其收益行為的界分節點,以及幫助者主觀明知和「通謀」的產生時間與內容對罪名認定的影響,從而區分易混用的罪名。
首先,判斷以虛擬貨幣轉移的物件是否具有犯罪所得的三個特徵,即財產性、刑事違法性、確定性。其次,以詐欺罪既遂為分界點,界定虛擬貨幣結算支付行為是掩飾、隱瞞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行為,還是上遊電信詐騙的幫助行為。最後,應以幫助者是否與他人事前通謀,是僅認識到他人在非法利用資訊網路展開犯罪活動或明知他人詐騙,認定虛擬貨幣結算支付行為是否構成電信詐欺罪的共犯。
綜上,虛擬貨幣結算支付型幫助行為的犯罪認定共有三種情形:
第一是幫助者在詐騙行為實行終了前未與他人通謀,在詐欺罪既遂且詐騙者取得具有財產性、違法性與確定性的財物後,故意為其提供虛擬貨幣結算支付的幫助,行為構成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
第二是幫助者雖然在客觀方面實施了掩飾、隱瞞了犯罪所得的行為,但在詐騙行為實行終了與他人就詐騙形成了意思聯絡,其行為應被認定為詐欺罪的共犯;若幫助者在詐騙行為實行最終了與他人達成了以實施網路犯罪活動為內容的意思聯絡,其行為構成幫助資訊網路犯罪活動罪。
第三是詐欺罪未既遂或財物不具有犯罪所得的三特徵,但幫助者明知他人實施詐騙,提供虛擬貨幣結算支付服務的,應認定為詐欺罪的幫助犯;幫助者明知他人實施網絡犯罪活動,卻不知道具體實施罪行,應以幫助資訊網路犯罪活動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以下為文章全文:
虛擬貨幣結算支付型幫助行為是運用虛擬貨幣為他人實施電信詐騙提供財物轉移幫助的行為。為加強對電信詐騙及其協助行為的打擊力度,2021年最高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共安全部聯合發布《關於辦理電信網路詐騙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乾問題的意見(二)》(以下簡稱《意見(二)》),提出了在沒有事前通謀的情形下,幫助者明知財物為電信網路詐騙的犯罪所得及其收益,仍透過虛擬貨幣對其予以轉換或套現的行為構成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明確將此類行為納入全鏈條打擊電信詐騙違法犯罪活動的關鍵環節,有力遏製了相關犯罪的高發態勢。
然而,隨著治理活動不斷深入,《意見(二)》以是否「明知」與「事前通謀」區分此罪與彼罪的弊端也隨之顯現。由於虛擬貨幣結算支付型幫助行為具有超時空性,可能發生於電信詐騙實行中或既遂後,並且“通謀”和“明知”的程度也不盡相同,還產生於電信詐騙實施的不同階段,司法實務中出現了判定被轉移財物是否為犯罪所得的標準不統一,認定結算支付行為是詐欺犯罪還是贓物犯罪的規則不完善,主觀方面對行為定性的影響未釐清等問題,從而造成詐騙罪的幫助犯、幫助資訊網路犯罪活動罪,以及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適用易混淆的困境,影響了刑法對此類行為的精準打擊,不利於電信詐騙的長效治理。
為明晰虛擬貨幣結算支付型幫助行為的認定路徑,依法對此行為進行懲治,應堅持主客觀相統一的原則、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有機結合犯罪構成要件的客觀方面和主觀方面,對犯罪情節進行全面的把握,避免片面地從客觀面或主觀方面認定犯罪,致使罪責刑不相適應。基於此,在虛擬貨幣結算支付行為的犯罪認定中,應把握犯罪所得的特徵,上遊電信詐騙與後續掩飾、隱瞞犯罪所得及其收益行為的界分節點,以及幫助者主觀明知和「通謀」的產生時間與內容對罪名認定的影響,從而區分易混用的罪名。
首先,根據刑法第六十四條「犯罪所得為犯罪者違法所得的一切財物」,判斷以虛擬貨幣轉移的對像是否具有犯罪所得的三個特徵,即財產性、刑事違法性、確定性。詳言之,第一,犯罪所得是財物,具有財產權,即可流通性和客觀的財產價值,但不以有體性為必要特徵,包括存款債權、股權等財產性利益。第二,犯罪所得必須由違法行為產生,具有刑事違法性,故不包含犯罪者因合法行為,民事違約或行政違法而取得的財物。第三,犯罪所得需歸屬於犯罪者,且涵蓋其「一切」違法所得,因此具有主體與金額兩方面的確定性。在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認定中,主體的確定性指犯罪所得已確實歸上遊犯罪的行為人所有;數額的確定性指犯罪所得的多少應以上遊犯罪的行為人最終取得的金額為準,不包含交易中所使用的資金,例如在冒充有資格人員推薦股票的詐騙類案件中,受害人向詐騙者交付的手續費或會員費是犯罪所得,而用於炒股、投資的資金最終不歸詐騙者所有,不應計入犯罪所得。據此,虛擬貨幣結算支付的財物符合以上三個特徵,才能被認定為犯罪所得,否則此類行為不可能被評價為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
其次,以詐欺罪既遂為分界點,界定虛擬貨幣結算支付行為是掩飾、隱瞞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行為,還是上遊電信詐騙的幫助行為。學界關於詐欺罪既遂的標準存在失控說、控製說與財產損失說的爭議,不過2018年最高人民檢察院公佈的《檢察機關辦理電信網絡詐欺案件指引》明確規定,電信網絡詐騙既遂的判定應採取失控說,即以被害人失去對被騙錢款的實際控製為標準。據此,上遊電信詐騙的既遂不僅意味著詐騙行為已經實行終了,還說明犯罪所得的主體與數額均已確定。因而,在既遂後發生的虛擬貨幣結算支付行為是典型的掩飾、隱瞞犯罪所得及其利益的行為。在既遂之前,即使被害人因產生認識錯誤而處分了財物,詐騙者也因此取得了財物,但由於詐騙行為仍在實行或財物還受被害人控製,無法確定最終的被騙數額,所以此階段發生的虛擬貨幣結算支付行為是上遊電信詐騙的幫助行為。以虛擬貨幣炒股詐騙類案件為例,被害人在被騙產生認識錯誤後先向幫助者轉移資金,以獲得用於在人為操控的證券平台炒股的虛擬貨幣,幫助者再將資金轉給詐騙者。然後,詐騙者會在證券平台調整股票漲跌,以讓被害人先部分獲利,後全部虧損的方式逐步非法佔有資金。在此類案件中,由於詐騙者取得財物後被害人還可以在平台上透過買漲買跌的方式控製資金,所以詐騙罪還未既遂,虛擬貨幣結算支付行為不可能構成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
最後,應以幫助者是否與他人事前通謀,是僅認識到他人在非法利用資訊網路展開犯罪活動或明知他人詐騙,認定虛擬貨幣結算支付行為是否構成電信詐欺罪的共犯。具體而言,其一,以幫助者是否事前通謀,認定掩飾、隱瞞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行為是構成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還是詐欺罪的共犯。其中,「事前」指犯罪實行終了前;「通謀」指幫助者與他人形成意思聯絡,但不等同於「共謀」,即不需要雙方就犯罪進行謀劃協商。在電信詐騙案件中,若幫助者在詐騙實行終了前,與他人就詐騙形成了通謀,應以詐欺罪的共犯追究其責任。在詐騙實行終了後,即使幫助者與他人就此次詐騙進行共同謀議,也不構成承繼的共犯,其行為僅構成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此外,從現有的司法解釋來看,片面共犯不構成詐欺罪的共同犯罪。因為,2016年最高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與公共安全部頒布的《關於辦理電信網路詐騙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乾問題的意見》與《意見(二)》改變了此前隻要提供費用結算的幫助者明知他人詐騙,就以共犯論處的做法,強調對犯罪所得及其收益予以轉現、套現、取現的行為構成共同犯罪應以有事前通謀的情節為前提,故單方面具有共同犯罪故意的幫助者不構成共犯。其二,若虛擬貨幣結算支付行為被定性為上遊詐騙的幫助行為,應以幫助者是明知他人實施詐騙,還是僅明知他人在網絡上實施犯罪,區分詐欺罪的幫助犯與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在具體案件的審理過程中,「通謀」「明知」的證明應綜合客觀證據,包括幫助者的生活經驗、與電信詐騙人員的聯絡管道與內容、結算支付的時間與方法、獲利情況等證據,然後據此對行為進行定性。
綜上,虛擬貨幣結算支付型幫助行為的犯罪認定共有三種情形,第一是幫助者在詐騙行為實行終了前未與他人通謀,在詐欺罪既遂且詐騙者取得具有財產性、違法性與確定性的財物後,故意為其提供虛擬貨幣結算支付的幫助,行為構成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第二是幫助者雖然在客觀方面實施了掩飾、隱瞞了犯罪所得的行為,但在詐騙行為實行終了與他人就詐騙形成了意思聯絡,其行為應被認定為詐欺罪的共犯;若幫助者在詐騙行為實行最終了與他人達成了以實施網路犯罪活動為內容的意思聯絡,其行為構成幫助資訊網路犯罪活動罪。第三是詐欺罪未既遂或財物不具有犯罪所得的三特徵,但幫助者明知他人實施詐騙,提供虛擬貨幣結算支付服務的,應認定為詐欺罪的幫助犯;幫助者明知他人實施網絡犯罪活動,卻不知道具體實施罪行,應以幫助資訊網路犯罪活動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另外,為依法嚴懲與防治電信網路詐騙及協助行為,在明確刑法適用與犯罪認定規則的同時,還需要秉持綜合治理與源頭治理的思維,在刑法規製以外運用新型技術強化對虛擬貨幣流通的監管,當違法行為發生時及時對資金的轉移採取攔截措施,並且加強反電信詐騙、虛擬貨幣交易炒作與非正規網路平台投資風險預警的宣傳教育,從根本上預防電信詐騙與虛擬貨幣的違法使用,保障人民的網路資訊安全與財產安全。
[本文係最高人民法院2023年司法研究重大課題「『兩卡』案件所涉幫助資訊網路犯罪活動罪的司法適用與政策完善研究」(ZGFYZDKT202310-03)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