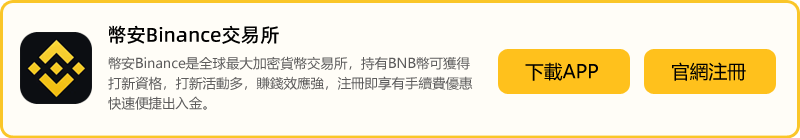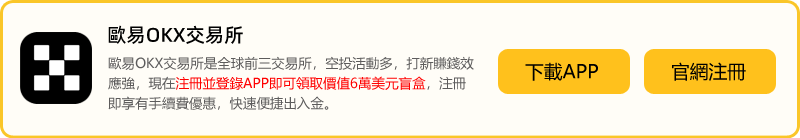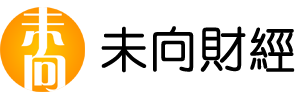《蔡钰·商业参考2》李迅雷:中国经济转型难在哪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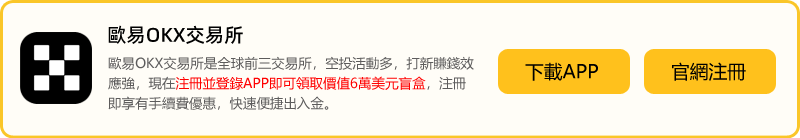

中国要加快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这事已经是共识了。而这个转型又分成两层:
第一层,是外循环不畅通的时候,当务之急就是把国内大循环给弄顺畅,这就需要发力扩大内需;
第二层,内需又分成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投资在短期能够稳增长,但长期看的投入产出比是不断下降的。所以,相对来说消费需求更值得去拉动。
我们提到过好几次,中国要让中等收入人群翻倍到8、9亿,就是为了增加有消费能力的人群规模。
最近我读到经济学家李迅雷的一篇文章,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经济转型的难点在哪里?
这是一个我很喜欢的牛顿第一定律式的问题。这相当于是在问,什么在阻碍中国顺利地实现经济转型,把消费需求大幅拉起来?
李迅雷给出了两个他认为比较关键的难点,我们来看看。
第一个难点是居民收入结构存在不合理。
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优势来自人口红利,这个你也知道。那人口红利的实质是什么?就是劳动力资源丰富而且廉价。体现在整个国家的GDP里,就是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占比很低。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1年这个数字只有43%,你别觉得听着挺高的,实际上,全球平均水平能够高达60%。而美国更高,超过80%。
如果我们去看中国的政府部门的税收结构,就会发现,中国政府收税更依赖企业而不是居民。这也好理解,毕竟中国过去那么多年,经济增长主要是来自投资和出口的拉动,而这两个动作的行为主体当然都是企业。所以,中国的税收总收入里,跟企业部门有关的要占到65%,而跟居民部门有关的大概是15%,其中个税的占比更低,只有7%。这之外,中国也没有资本利得税、房产税和遗产税这三大跟居民相关的基本税种。
你可能听到这句话,火气蹭就上来了,好好的我干嘛替政府琢磨多收你的税。你先按捺住,再来听听美国。
美国联邦政府的税收结构刚好跟中国是倒过来的,2020年美国的个税占比达到47%,而企业所得税占比只有6.2%。
这两年疫情,美国财政不是一直在给美国的居民发现金补贴,还给给失业人员发放巨额的失业救济金么。结合它的税收来源来看,就等于是从中高收入者那里收税,然后发放给全体美国居民,等于说,财政的居民收入再分配的功能还挺强。
这来带来的结果你已经看到了,虽然疫情爆发,但美国民众这两年还是很愿意投资,很愿意消费,以至于通胀率到了3月份都拉到了8.5%。美股也一再创新高,资金们还纷纷参与SPAC公司去并购项目。
而中国这边,因为税收主要来自企业部门,所以这两年的降税减费行动也主要是针对企业部门,比如说给1.5亿户的市场主体退2.5万亿的税金等等。而我们直接给到居民部门的减税或着补贴动作不算多。
那为什么哪个部门交税多就要给哪个部门退税也多呢?凭什么不能够拿企业交的税来补贴穷人呢?政府也有政府的考虑,它得优先保护社会的主要税基,也就是纳税主体,只有这样明年它才能够仍然有税收来让社会持续运转。不过最近也有消息开始说,像北京这样的城市也要开始发居民消费券,直接补贴居民了。
那么,要拉动内需,政府干脆搞阳光普照,直接给全市场注入流动性不行吗?这不就能把居民和企业都照顾到了。
这也不太可行。李迅雷说,货币总量是持续扩张了,但结果一般都是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中的高收入人群受益,而中低收入的居民明明更需要钱,但在这种广泛撒钱的过程当中,他们的相对收入却会变得更少。有统计数据说,2020年开始,三年疫情下来,居民部门的收入差距是在进一步拉大的。拉大的原因就是,中低收入者们主要干的是劳动密集型的工作,更加需要跟他人和社会打交道,进行近距离接触,所以他们也就更容易受到疫情的影响而被动歇业。
所以关于这一点,李迅雷的结论是,中国经济要往拉动内需转型,首先就得通过税制改革来缩小收入差距。那怎么缩小收入差距呢?得想办法对高收入者实行有效地征税,把政府税收收入里的个税比重提高,然后通过第三次分配,来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和社会福利。
但是这个道理大家虽然明白,但是毕竟牵动所有人的利益,说易行难,所以也就成了中国经济转型的第一个难点。
第二个难点是,人口老龄化可能导致创新的动力不足。
这件事很好理解了,我们只简单来看一看李迅雷所采用的论证数据。
他预计说,2022年,中国的总人口就会开始减少。
那么,中国要是没有了人口红利,可以靠工程师红利,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人才红利来创新吗?你肯定也经常听说,中国的大学生产量是非常高的。那么,用什么来衡量工程师红利这个东西存不存在,是在上升还是在下降呢?
李迅雷选了一个评估指标:劳动生产率的增速变化。所谓「劳动生产率」,就是单位劳动力的价值产出的多少。你想,这个指标还挺有道理的:一个单位劳动力,比如说一个人,他在劳动力可以投入的体力是相对固定的,但是他的脑力,如果他经过了更多的教育是可以不断地提高的。这样一来,他所创造的价值越大,当然也就能够说明工程师红利越存在。
结果,李迅雷的研究结论是,工程师优势我们是有的,但工程师红利不好说。人口红利消失之后,大学毕业生的数量估计也会在明年开始达到峰值,而到了20年后,中国大学毕业生的数量连现在的一半都达不到了。
而相对来说,真正有工程师红利的可能是美国,美国在2021年人口增速也很低,只有0.1%。但它靠的是每年在全球吸引超过100万的优秀年轻人赴美留学。这使得他整个国家的平均年龄能够保持在38岁左右。
我查了一下,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下来,中国人口的平均年龄是38.8岁,跟美国现在差不多。但是中国的外来移民并不普遍,留学生的数量也还比较少。
所以李迅雷的意思是,开放移民这事也需要加紧。否则像日本那样,在人口已经充分老龄化之后才积极鼓励移民,就为时已晚了,日本今天的创新动力跟它30年前相比,已经明显不足。这也说明了,人口结构越年轻,才越具有创新动力。
而中国的高端劳动力,跟日本和美国相比还有一个区别,就是更爱从事金融业而不是科技和先进制造,哪怕是工科类学生也愿意往金融行业去。这就等于说,金融业对中国形成工程师红利也有干扰。
所以,中国想要产业升级,得在户籍制度、移民政策等等诸多方面进行改革,来给产业提供创新人才,这件事也非常难、非常艰辛。
但是难也得做啊。所以借着李迅雷的这两个思考角度,接下来,你要是看见中国探索资本利得税、房产税和遗产税,或者去尝试接收更多的留学生和移民,你就知道背后的考虑是什么了。
另外,李迅雷的这两个思考还制造了一个冲突:
你想,中国产业升级需要依靠人才创新,而有产业创新能力的人才,往往又是中高收入群体,因为他收入高才证明他的能力有市场价值。这样一来,如果加大对这群人的征税,可能又会打击他们的创新动力。
也就是说,前面说的两个难点结合在一起,又会形成互相咬合的第三个难点。
所以我不负责任地猜测一下的话,如果要在个税层面进行改革,可能会更侧重面向财富税基征税。
什么意思呢?国际上主流的税基可以分成三类:国民收入、国民消费和国民财富。
把国民收入当税基,就是从你新挣的钱里收税;
把国民消费当税基,就是从你新花的钱里收税;
把国民财富当税基,就是从你囤积的钱里收税。
你想,要是从你的日常收入里多征税,容易影响你的工作热情,这不利于社会发展和创新;那要是从你日常消费里征税,又容易影响你的消费热情,这也不利于拉动内需;相对而言,要是从你的财富里面征税,也就是房子、遗产和股票收益这些,它不太会打击劳动生产率,而且还可能有鼓励消费的效果,因为可能就会觉得,花掉的钱才真正属于你。
好,听到这儿,如果你想去花一花钱?请告诉我你打算去买点什么。
再见。